二○一二年
路過早上八點的大成街,擁擠著服裝、飾品與各類小店的一百多公尺街道,只有一間剛拉開鐵門。
這大概是全台灣最迷你的二手書店,用紅漆寫著「中外書店」的鐵捲門一拉開,入眼就是滿滿的書。不到六坪大的空間以書為牆,用書架隔成側躺的「日」字型,站在店中央轉一圈,所有的書在視線範圍二公尺內盡收眼底,後背包還會被書架卡住。
 |  | 中外書店空間不大,門面的層疊書牆,
像也擠壓著時間。 | 中外書店密密紮紮疊滿書。 | | | |  | | 不到三坪大的空間以書為牆。 |
三年多前初訪時問坐在門口顧店的阿嬤:「你們這邊賣哪些書?」她白我一眼:「都在這裡,不會自己看?」 讓我頓時覺得自己問了個蠢問題。
縱使拉開鐵門,從外頭透進來的微弱日光僅照亮書店一小角。綿長時間似乎被壓縮在層層書頁裡,店裡一片昏暗,以陳舊木梯連接著的二樓,傳來桌椅挪動的聲音與模糊說話聲。
「老闆在嗎?」我對著二樓喊了幾聲,過了十多分鐘,一雙穿著包鞋的腳顫巍巍探下來,喀碰喀碰地一階階踩上地面,一隻手擰亮店裡的燈,「啊,這麼早。」
裹著大衣毛帽的他比記憶中更瘦小單薄,我還是慣稱他老闆,雖然他說老闆是他朋友,也就是常在門口顧店的那位阿嬤。
「找什麼書嗎?」「沒有,就路過進來看看。」
「喏,妳就慢慢看。」他點點頭,緩緩走到對面街上。清晨下了場雨,地上仍濕漉漉的,店外掛的「祖傳AB型肝炎藥」在冰冷空氣中緩緩搖晃著。
「For some time we have felt……」陳爺爺抓著手上的紙一字一句地唸,發音挺標準,音節鏗鏘有力,大清早聽起來特別清朗。
「是您自己寫的嗎?」等他唸完,我向他借文稿來看。是很漂亮的書寫體,原本的鉛筆字褪了色,又以原子筆覆上一層。
「是啊,是我寫的。」他又不知從哪抽出一本英文書,綠色封皮寫著「The Life of Christ」。他輕輕撥開泛黃的紙頁,說,這我都會讀。
 | | 英文書難不倒陳爺爺。 | | |  | | 這間小小書店,是陳爺爺後半輩子的家。 |
取名叫「中外書店」的小書店,顧客確實涵蓋中外。陳爺爺小學畢業,對語言很有興趣的他自學日文,五十多年前開了這間書店,認識一位外國人R先生,與他結為好友,又靠對話與翻字典加強英文。「我一開始也不懂,但很敢問。」
語言優勢讓他多了外國客源。陳爺爺說,當年台灣購買幻象戰機,幾位隨機來台,駐紮新竹空軍基地的法國機師想找小說解悶,找遍新竹才在這買到屬意的書。書店後來慢慢打出名氣,外國人想找本便宜的外文書,仍會想辦法拐進街巷,從幾十間店面中找出這間小店。現在最靠近店門口的長型架子,外文書仍擺在與視線同高的最顯眼位置。有民國七十幾年出版的《簡愛》,也有《哈利波特:火盃的考驗》。
但書店還是以收購參考書為主,三年前和顧店的阿嬤聊天,她就說「一綱多本」後生意難做,以往還有客人特別從金門訂書,現在買進容易賣出難,書愈積愈多。
看著架上泛黃脫落的「圖書閱畢歸還原處」字條, 這三年來網路、電子書、平板電腦這麼發達,課本書冊更新這麼快,這架上的線性代數、電子學、歌本樂譜、翻譯小說,不知道幾年沒人翻過了。
書店客人愈來愈少,太過昏暗潮濕的空間使書況不甚理想,靠大門那排的書不少都泛黃長霉斑,裡側的參考書年份大概可以追溯到我爸的學生時期。書與書架似乎構成一座小小的堡壘,作息起居延伸進店面,我幾度遇到阿嬤,她正邊吃飯邊看電視,有次在刷牙,讓我一時不知該作何反應。
「您今年幾歲了?」我問陳爺爺。他扳著手指說:「我比李登輝年長兩歲。」
那就是九十一歲。我很想知道更多有關書店的事,但他跟我說了另一個故事。
他說,他年輕的時候認識一位很認真的孩子。那孩子姓梁,在家裡四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,母親賣杏仁豆腐,家裡窮得不得了,但他很愛看書,沒事就到店裡翻翻書。
他先考上師範學校,派到尖石鄉服務兩年,那裡時常斷電,交通很不方便,卻是很好的念書環境。他在那裡發憤圖強,存下來的錢買英文唱片自學。很有數學天份的他,後來考上清華大學。
「他國文五十五分,三民主義三十八分,英文八十五分,數學八十九分,他常來我這兒翻書學英文。」陳爺爺瞇著眼背出四十幾年前梁同學的聯考成績,臉上神情很驕傲。
陳爺爺說,梁同學現在在美國俄亥俄州教書,他幾年前病了,梁同學回台灣時特別來找他,在他手裡塞了幾張美鈔,「這次我不是來買書,是來看您的。」
「這些錢我都還留著,沒去換過。」陳爺爺的聲音愈說愈低,我不知道他說的是不是真的,還是他把很多故事混在一起說。
快九點了,我和善嬿約九點在火車站前集合,但他又說要告訴我另一個故事。
「爺爺您電話幾號?我回去再跟您聯絡。」我還是很想聽其他關於書店的故事,而且想起他剛剛扳著指頭數年紀的樣子,突然覺得記憶像個沙漏,來不及記下的,瑣碎但重要的事,隨著時間一點一滴流失。
陳爺爺給我號碼,揮揮手,「要再來啊」。
回到嘉義後,我撥了通電話給陳爺爺。他在話筒另一端嚷著他耳朵不好,要我再大聲點,但最後還是無法順利溝通。
我喊,我前幾天一大早去您書店,您還記得嗎?
他喊,妳說什麼時候要來?什麼時候要來啊?
下次去新竹,我還想再聽陳爺爺說書店的故事。
等等我吧。
二○一六年
中外書店收了。
大成街四十九號成了服飾美甲店,嶄新裝潢在燈光下閃著粉紅色,曾經往上堆疊到天花板的書,現在是往店外延伸的衣服。
這五年間,我斷續去了幾趟新竹,但每次都匆匆來去,始終沒繞去書店一趟。其實距離不遠,但總想著下次、下次再去吧,拖著拖著,直到得知書店在半年前歇業的消息。
我也終於知道陳爺爺的名字,他叫陳守貞,搬到散步距離大約半小時遠的一間私立養護中心,離大成街的生活圈不算遠,現在里長和商圈的老朋友輪流去看他。
 | | 住在養護中心的陳爺爺,見到有訪客,精神都來了。 |
今年是暖冬,這天穿短袖在街上走也沒問題,陳爺爺卻穿著淺咖啡色的毛衣,外頭罩著一件寒流才會拿出來的黑色羽絨外套。層層衣物裡的他,比記憶中更小了。聽到我要找他,陳爺爺轉頭看著我,眼睛亮起來。
「您還記得我嗎?」我驚喜地問。
「不記得。」
他只是開心有訪客,原本排定要去的復健也不去了。我握著他的手重新自我介紹,他的手乾燥溫暖,就像外頭的陽光。
陳爺爺說,身體愈來愈不行,爬不上樓梯,後來連抬腳都力不從心,在店裡跌倒兩次。他半年前收起書店,搬進安養中心,覺得體力愈來愈差,雖然耳朵、眼睛挺好,思緒也還清楚,但他走不動,被困在九十五歲的軀殼裡。
那些書呢?「通通送人,有些就算想送也沒人要。台灣人也不怎麼看書了,都在那邊滑、滑、滑。」陳爺爺伸出食指,在空中撇了三下,歲月的瘢痕佔領他的手指。
這次,他終於好好說了自己的故事。
他是廈門鼓浪嶼人,小學時在教會辦的學校學過幾年英文,他喜歡學語言,但開始打仗後什麼都中斷。
他從軍去過四川,也曾在重慶的教會機關幫忙辦報紙,提起戰亂中被土匪打死的母親,他眼淚大顆落下,哭得說不出話。講到在重慶久咳不癒,一位醫生幫他針灸治療,醫生娘每天都拿雞蛋給他吃,他堅持寫下恩人名字,筆畫在紙上飄蕩、墜落,最後塌成一團。他把筆一丟,臉陷進手掌裡:「我想不起來……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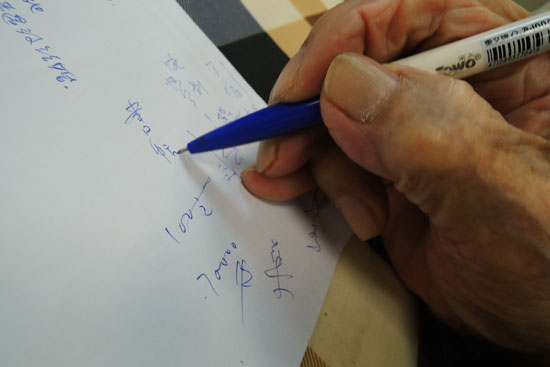 | | 陳爺爺堅持寫下每位幫助過他的貴人名字。 |
來到台灣後,他揀美國人留下的外文書賣到牯嶺街,攢起一點小資本。後來幫開書店的朋友寫訴狀,得到為數不少的書,到新竹創業。「新竹好,比台北樸實得多。」
他從小攤車做到大成街的店面,很多外國人和學生到他店裡買書,他又說起那個姓梁的孩子,「他國文五十五分,三民主義三十八分,英文八十五分,數學八十九分……」
我不知道他當年為何要否認自己是書店老闆,後來和陳爺爺的鄰居、朋友聊起來,才知道白色恐怖時代在他身上烙下看不見的傷痕。身為一位開書店的外省知識分子,他極力不讓自己引起別人注意。長年活在遭人舉報的壓力下,在解嚴三十年後,他仍有種下意識的、對自身身分的自我審查。
陳爺爺曾差點成為異國女婿,一位香港友人邀他去薩摩亞──就是那本人類學與社會學史上最暢銷著作《薩摩亞人的成年》裡的薩摩亞──那裡有著整片藍綠色軟玻璃一般的、溫暖的海,一戶西薩摩亞的人家想把女兒嫁給他,女孩有雙美麗眼睛與豐潤的褐色皮膚,但他沒有留下來。
「當地醫療太不方便,」陳爺爺說,嘴裡隱隱滾動著其他沒說出口的原因,「感情的事,不要看得太認真。」
他的後半人生回歸新竹的小書店,有鄰居好友陪伴,沒有孩子。
陳爺爺說了很多很多,說到吃飯時間都過了。他努力回憶著家鄉的模樣,國共內戰的往事,堅持寫下他生命中所有恩人的名字,但多半成為散落在紙上的筆劃碎片。
「妳要是早點來,我還可以送妳書,告訴妳很多很多事。」臨走前,他溫暖的手與我相握,「下次再來吧」。
我點點頭,「下次再來」。
中外書店
新竹市大成街49 號(已歇業)
※ 文章出處/資料提供:山岳文化 |